 收藏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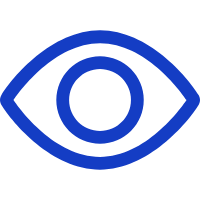 1203
1203 原告:王某甲,男,1951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西玲,福建通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晏英,福建通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某甲公司,住所地江西省高安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乙。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宇,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守明,福建智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某甲与被告某甲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8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某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西玲、晏英,被告某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昊宇、蔡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某乙公司支付王某甲工程款7898510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工程款789851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LPR,自2021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4年7月30日为975696元),合计8874206元。二、判决由某乙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审理期间,王某甲诉讼请求第一项变更为:一、判令某乙公司支付王某甲工程款4429157元以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工程款4429157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LPR,自2021年1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算至2024年7月30日为578847.71元),合计5008004.71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王某甲与案外人某丙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签订协议,约定由王某甲承建某丁公司开发的宁德市××路×××××项目二号地块工程(以下简称二号地块工程)。二号地块工程名义上以某乙公司承建。王某甲安排钟某某参与现场施工。2014年12月2日,某丁公司、某乙公司、宁德市××路商业街二号地块施工班组(实际由钟某某签订)签订《三方协议书》,对二号地块工程各方应承担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其中第3条约定:二号地块工程款由某丁公司转入某乙公司,再由某乙公司转入二号地块工程施工班组指定的收款账户;第6条约定二号地块工程单独办理竣工结算。二号地块工程于2016年1月18日竣工验收。2016年4月13日,经钟某某与某乙公司核对,王某甲共收到二号地块工程的工程款分别是:由某乙公司转入的工程款为65876660元;由某丁公司直接转入的工程款为850万元;某丁公司转到其他劳务公司再转给王某甲的工程款为520万元,以上合计79576660元。另某丁公司代付货款577万元、水电费64247元、某乙公司的交接费用2223544元(该笔费用中某乙公司尚有农民工工资押金8万元未退),以上合计8057791元。双方对账之后,某乙公司分别又于2016年6月14日、2016年7月21日、2017年1月22日、2018年2月13日分别转入468100元、234080元、2303400元、130万元,合计4305580元。2018年8月9日,某丁公司与王某甲签订《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确认二号地块工程的工程总造价为105263839元,王某甲和钟某某在该确认书上签字。王某甲从某丁公司得知,某丁公司已与某乙公司结算完毕并已全部支付工程款。鉴于针对本案二号地块工程的工程款某丁公司已全部支付某乙公司,但某乙公司并未依约向王某甲支付完毕。根据《三方协议书》,本案二号地块工程扣除企业所得税1.8%,营业税4.56%,但王某甲认为营业税约定标准过高,根据公司惯例,营业税缴税标准通常为3.43%,故二号地块工程应扣除的税费为105263839元×(1.8%+3.43%)=5505298元。至于协议中约定的1.5%的管理费,王某甲认为,某乙公司并未在王某甲施工过程中履行组织、管理和监管的责任,无权收取管理费。因此,二号地块工程某乙公司至今仍欠付王某甲工程款7898510元(结算价105263839元-已付工程款79576660元-已付工程款4305580元-代付货款、应付水电、交接费用8057791元-税费5505298元+未退的农民工工资押金8万元)。审理期间,发现王某甲与某乙公司签订有《以房抵工程款协议》一份。根据协议约定,某乙公司应抵扣王某甲工程款3469353.31元。故作出上述变更诉讼请求。
某乙公司辩称,一、本案案由应当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二号地块工程实际由某丁公司发包给某戊公司(简称某己公司),某乙公司作为名义上的施工人,与某己公司存在挂靠合同法律关系。某乙公司仅向某己公司收取管理费。因此,本案案由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而非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二、王某甲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首先,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二号地块工程由某丁公司分包给某己公司,某乙公司仅与某己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王某甲作为某己公司的签字代表,与某乙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根据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9民终925号生效判决认定:“王某甲作为某己公司依法确定的代表人,其以某己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某己公司承受,《补充协议》对某己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某己公司基于《补充协议》具有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的法律地位。”足见某己公司才是二号地块工程的承包人,王某甲仅是某己公司的法定负责人,代表某己公司签署合同和其他文件。最后,王某甲在该(2023)闽09民终925号一案中,也否认其为二号地块工程承包人,且没有证据表明王某甲是实际施工人。因此,王某甲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三、某乙公司已履行挂靠义务,并按照合同约定扣除管理费、税费。某己公司无权要求退还已支付某乙公司的管理费、税费。首先,某乙公司已按照《补充协议》《三方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有权向某己公司收取合同约定的管理费和税费。其次,对挂靠合同中约定的管理费处理,应当采取自然债务的处理规则,管理费已经实际支付的,支付管理费一方主张返还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四、二号地块工程已由某乙公司与钟某某结算完毕,某乙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全部支付二号地块工程款。某乙公司作为被挂靠单位,在履行与某己公司的挂靠合同过程中,已与钟某某结算完毕。由某丁公司转给某乙公司的二地块工程款已根据钟某某的要求支付完毕,不存在任何未结欠款。
根据当事人庭审陈述及审查认定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1.某己公司于2002年4月12日设立,由王某甲担任负责人至2022年12月8日。
2.2014年1月24日,某乙公司被某丁公司确定为宁德市××路×××××(二标段)工程中标人。2014年1月25日,某丁公司(发包人)与某乙公司(承包人)签订《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某丁公司把工程名称为宁德市××路×××××(二标段)工程(Ⅱ地块、Ⅳ地块,3#、4#、9#、10#、11#、12#楼)交由某乙公司承建。
3.2014年,甲方某丁公司作为发包方(签名处公司盖章),乙方“某己公司(王某甲)”作为承包方(“签字代表”是王某甲),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开发的宁德市××路×××××项目二号地块工程由乙方承建,甲方与某乙公司签订了《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该合同同样适用于乙方。就原合同,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补充约定如下:乙方同意,甲方发包给乙方二号地块工程,名义上仍以某乙公司名义承建,即建筑施工许可、竣工备案、三算单等与该工程有关的所有文件(含官方文件、证件)仍以某乙公司名义办理,乙方所承担该工程有关文件办理或者协助办理义务仍按原合同的约定执行;鉴于本项目二号地块工程的相关官方文件、有关手续等以某乙公司名义配合或者负责办理,乙方同意向某乙公司支付如下费用:管理费1.5%,取费基数按税前造价,企业所得税1.8%及营业税代收待汇交地税4.56%,取费基数按工程总造价,此费用在甲方支付给某乙公司乙方完成的合格工作量中扣除,对此,乙方同意该费用实际由乙方承担。
4.2014年12月2日,甲方某丁公司(签名处公司盖章)、乙方某乙公司(“签字代表”是付某某,加盖公司合同章)、丙方宁德市××路商业街二号地块施工班组(“签字代表”是钟某某)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甲方开发的宁德市××路×××××项目由乙方承建,双方签订了《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将本项目的二号地块工程分包给丙方施工。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三方对原合同补充约定如下: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项目二号地块工程分包给丙方施工;2.丙方分包的二号地块工程,名义上仍为乙方承建,即建筑施工许可、竣工备案、三清单等与该工程有关的所有文件仍以乙方名义办理,乙方所承担该工程有关文件办理或者协助办理义务仍按原合同的约定执行;3.乙方同意按原合同约定的乙方应履行配合或管理义务外,对另行分包的二号地块工程,还应履行如下义务:协助丙方办理工程款申报审批及工程结算的相关手续,并依据完成的工作量开具相应税票;协助丙方办理完成工程所有内页资料审查、盖章及归档工作;为丙方提供有关本工程项目对外联系签字、盖章及函件的办理,对上级领导部门检查予以配合;负责对丙方使用的设备做好交接工作,并在设备移交之前办理完设备租用的结算费用。4.就上述乙方对丙方所承担的相关配合及管理等义务,甲方同意在支付二号地块工程款时,从应支付工程款中扣除管理费1.5%、企业所得税1.8%及营业税代收代汇交地税4.56%支付给乙方。工程竣工验收办理结算后,再按结算工程造价增减以上费用。所有工程款由甲方转入乙方账户,扣除相关费用后再由乙方转至丙方指定的专用账户(账号:6217********,户名:黄某某;开户行:建行福州市成北支行)。5.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应提交80万元履约保证金给乙方,按原合同约定甲方退还乙方银行保函,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退还丙方的80万元履约保证金,丙方应提交8万元农民工资保证金给乙方,按规定劳动局退还保证金,乙方在三个工作日内退还丙方的8万元保证金;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二号地块工程另行分包,重新发包后的二号地块工程的工期、质量、安全均与乙方无关。原合同范围内继续由乙方施工的工程内容应单独组织竣工验收、单独办理竣工结算,甲方不得以二号地块的工期、竣工资料归档问题等任何理由拖延乙方办理竣工验收与竣工结算,对此,甲方乙方均无异议。”本协议签订后,丙方向乙方交纳工程履约保证金80万元、农民工资保证金8万元。
5.2015年4月8日,甲方某乙公司作为总包方(签名处是公司合同章),乙方“王某甲建筑项目部”作为分包方(“签字代表”是王某甲),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某丁公司开发的宁德市××路×××××项目由甲方承建,双方签订了《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甲方将已施工的原施工合同中除水电安装工程之外的所有剩余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经双方协商,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如下补充协议:甲方将原施工合同中除水电安装工程以外,已施工剩余的工程内容分包给乙方施工,同时乙方执行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内所有内容。
6.二号地块工程于2016年1月18日通过竣工验收。
7.2016年4月13日,某乙公司作为总包方(“签字代表”是付某某),分包方宁德市××路×××××二号地块施工组作为分包方(“签字代表”是钟某某),双方共同制作《宁德市××路×××××二号地块工程款结算总表》,记载:1.总包方应收工程款总额9529万元(根据合同);2.分包方已收工程款65876660元(附明细表);3.建设方转分包方850万元(35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4.建设方转劳务公司再转分包方520万元(300万元+220万元);5.总包方代扣税费6060444元[9529万元×(1.8%+4.56%)];6.总包方代扣管理费1429350元(9529万元×1.5%);7.建设方代转钳固商品砼款577万元(217万元+360万元);8.总包方交接费2223544元(1850994元+372600元,附明细表);9.项目经理工资17万元;10.总包方扣水电费64247元;11.未收取工程款余款-4245元。2016年6月14日、2016年7月21日、2017年1月22日、2018年2月13日,某乙公司分别转入方峥嵘账户468100元、234080元、2303400元、130万元,合计4305580元。
8.2018年8月9日,甲方某丁公司(“签字代表”是丁某某)、乙方“某己公司(王某甲)”(“签字代表”是王某甲、钟某某)共同签订了《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2)》约定:甲方开发的宁德市××路×××××工程项目,由某乙公司总承包,由于总承包方工程进度延后,总承包方与甲方双方协商同意,将宁德市××路×××××项目二号地块工程交由乙方(施工班组)施工,总承包方不变。现就工程结算造价事宜,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在2018年2月3日已确认的《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的基础上共同确认如下:一、工程总造价在101909379元基数上增加375595元;二、垂直运输增加费399019元;三、总包管理及配合费279846元;四、工程赶工费双方协商金额230万元;五、以上四项合计金额为105263839元,此金额已包含乙方完成“原合同”、“补充协议”、奖励金额、管理配合费、工程增加费等一切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所有费用,双方不存在任何遗漏和未结清的费用。
9.2018年12月19日,甲方某丁公司(签名处公司盖章)、乙方某乙公司(签名处公司盖章)、丙方宁德市××路×××××二号地块施工班组代表(“签字代表”是王某甲、钟某某)共同签署了《以房抵工程款协议》,协议约定:甲方、丙方同意用坐落于宁德市“天茂·城市广场××号楼××房屋抵丙方应收取工程款3469353.31元。附双方确认的《以房抵工程款清单》,记载:宁德市××路×××××二号地块施工班组欠工人工资,用宁德市××路×××××2号楼房屋抵工人工资3473367元。
10.某乙公司于2019年10月17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某丁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19)闽09民初505号,某乙公司提出诉请:1.判决某丁公司向某乙公司支付一标段、二标段(含二号地块)工程款94929857.5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以实际工程欠款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判决某乙公司有权就欠付工程价款项对案涉工程享有工程款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鉴定费由某丁公司承担。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2013年7月10日,某丁公司对宁德市××路×××××工程进行招标。招标文件中规定:工程分1-4四个地块,共有一层地下室(局部两层)、一至二层集中商业及商业步行走廊、8栋高层组成;工程分成两个标段招标,其中一标段包括一号地块(1、2号楼)、三号地块(5、6、7、8号楼)加××路北段地下室商业;二标段包括二号地块(3、4号楼)、四号地块(9、10、11、12号楼)。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24日,某丁公司先后向某乙公司出具一标段、二标段工程《中标通知书》。……其中二号地块工程曾由某乙公司经某丁公司同意分包给某己公司实际施工,具体系由某丁公司、某乙公司及某己公司的钟某某施工班组于2014年12月2日签订《三方协议书》,约定二号地块工程分包给钟某某施工班组施工,二号地块单独竣工验收,单独办理竣工结算。……”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6日作出判决:“一、某丁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3692467.7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3692467.76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7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二、某乙公司在上述工程款本金13692467.76元的范围内,对其承建的本案讼争工程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三、驳回某乙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某丁公司的反诉请求。”判决后,某乙公司、某丁公司均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年8月3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上述事实并作出判决:“一、维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民初50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二、撤销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第四项;三、变更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9民初50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某丁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乙公司支付拖欠的工程款13692467.76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2001297.3元为基数,从2020年1月1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利息以2001297.3元为基数,从2021年1月1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9689873.16元为基数,从2019年10月17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均按当期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四、某乙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丁公司支付工期延误损失315万元;五、驳回某丁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双方存在争议的是:王某甲作为本案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某乙公司认为,王某甲不是合同相对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首先,根据《补充协议》约定,二号地块工程由某丁公司分包给某己公司,某乙公司仅与某己公司存在挂靠关系。王某甲作为某己公司的签字代表,与某乙公司不存在合同关系。其次,根据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闽09民终925号生效判决认定:“王某甲作为某己公司依法确定的代表人,其以某己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某己公司承受,《补充协议》对某己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某己公司基于《补充协议》具有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的法律地位。”足见某己公司才是二号地块工程的承包人,王某甲仅是某己公司的法定负责人,代表某己公司签署合同和其他文件。最后,王某甲在该(2023)闽09民终925号一案中,也否认其为二号地块工程承包人,且没有证据表明王某甲是实际施工人。因此,王某甲不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
王某甲认为,本案王某甲具有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王某甲系本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相对方。1.综合本案的证据,《三方协议书》、二号地块物资盘点交接清单,签订时间均在2014年12月2日,且相关的二号地块施工班组提交的80万履约保证金、8万农民工资保证金也能与《三方协议书》对应;而在2016年4月13日,二号地块工程款结算总表(钟某某签字)中关于总包方交接费、总包方代扣税费也能与《三方协议书》对应。故《三方协议书》中宁德市××路商业街二号地块施工班组具有合同相对方的地位,而二号地块施工班组即是王某甲和案外人钟某某,钟某某本人确认由王某甲提起本案诉讼,故王某甲依据《三方协议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某乙公司也在其提交的判决书中确认王某甲、钟某某的实际施工人地位。2.《补充协议》《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2)》中乙方这样表述:“某己公司(王某甲)”,显然括号作用不可能是对前面内容的解释,因为公司和王某甲明显是两个不同主体,这里括号作用应当是“或者”,最终签字主体是王某甲,而不是某己公司,而某己公司也一直不承认系二号地块工程的分包人,并已针对某乙公司提交的该份判决书提起再审申请。因此,从《补充协议》《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2)》王某甲签字来看,王某甲同样具有提起本案诉讼主体资格。3.退一步说,即便某乙公司提交的该份判决书基于王某甲职务代表行为推定某己公司具有二号地块分包人的法律地位,但从二号地块工程款支付实际履行情况来看,某乙公司在收到二号地块工程款之后从未经过某己公司走账,而是直接转给施工班组,且在2016年4月13日某乙公司也是直接与施工班组钟某某进行对账,而从未经过某己公司。假设不存在《三方协议书》,二号地块工程施工班组(王某甲、钟某某)也与某乙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施工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更何况本案还存在三方协议书,而某乙公司提交的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并未否认《三方协议书》的效力。4.从工程款的交付情况来看,某丁公司将二号地块工程款转给某乙公司,某乙公司再转给二号地块工程施工班组,款项流转与某己公司完全没有关系。王某甲基于某丁公司已经将工程款支付某乙公司而要求某乙公司直接给付符合双方事实上的一贯做法。
本院认为,王某甲作为某己公司时任负责人以某己公司名义与发包方某丁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二号地块工程进行分包施工,从《三方协议书》可以确认取得总包方某乙公司同意,故某己公司具有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资格。《补充协议》订立后,某己公司在二号地块工程施工过程中陆续收取了某丁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办理竣工结算时,王某甲亦以某己公司名义与某丁公司完成了对二号地块工程的结算,《宁德市××路×××××房屋建筑工程二地块竣工结算确认书(2)》记载:“以上四项合计金额为105263839元,此金额已包含乙方完成‘原合同’、‘补充协议’、奖励金额、管理配合费、工程增加费等一切甲方支付给乙方的所有费用,双方不存在任何遗漏和未结清的费用。”由此可见,《补充协议》得到实际履行。在案证据显示,尽管王某甲、钟某某等人参与了二号地块工程具体施工,但均以某己公司施工班组进行施工,王某甲在二号地块工程的施工行为表明,并未取得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法律地位,故其以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主体不适格。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某丁公司把宁德市××路×××××项目二号地块工程分包某己公司时,某己公司把该工程挂靠某乙公司,二号地块工程经竣工验收,工程经结算,结算款为105263839元。本案王某甲参与二号地块工程具体施工,是以某己公司施工班组进行施工,不具有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法律地位,故其以二号地块工程分包人身份提起本案诉讼,诉讼主体不适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王某甲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俐兴
二〇二五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 陈巧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第七百八十八条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第一百二十二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五十七条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三)驳回起诉;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零八条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
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

推荐阅读
智能推荐
- 1 从票面额到票面税额的拟制逻辑,印证非法出售罪犯罪对象仅限空白发票
- 2 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 3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 4 一般纳税人登记新政落地,小规模纳税人如何合规应对?
- 5 新增值税法对企业租用个人房屋的税费影响
- 6 (2025)新2327民初3718号新疆XX有限公司;四川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 7 (2026)新40民终121号何某;汤某;刘某乙;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李某乙;卢某;李某甲;李某丙;王某二审民事判决书
- 8 (2025)辽行再19号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再审行政判决书
- 9 (2024)鲁15刑终257号孔某峰虚开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二审刑事判决书
- 10 (2025)宁04刑终81号 隋某;郭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刑事二审刑事裁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