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
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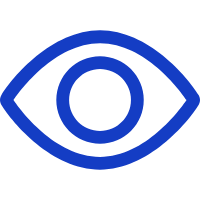 542
542 01、引言
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简称“两高解释”)自2019年由两高共同启动研究起草工作,到2024年3月颁布实施共历时近五年时间,期间还征求了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中央单位和全国法检系统的意见,可谓拉满了实务界和学界对这份解释的期待值。各界期盼新的解释能够有效指导虚开犯罪的司法实践,解决实务中类案不同判、罪责刑不相适应、出入罪规则不满足经济活动日新月异变化需求等各种“急难愁盼”的顽疾和弊病。
从两高解释出台到近期的反馈来看,尤为受到关注的还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有关条款,也是争论高发、争议不断之所在。两高解释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犯罪行为类型、出罪情形、此罪与彼罪的关系等规定在理解和适用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今年4月,最高法和最高检相继组织了官方天团针对两高解释撰写发表权威文章,意图解读疑难复杂条款的理解与适用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两高文章在虚开条款的认识和理解上却又出现了诸多差异和矛盾,不免令人担忧这份解释能否有效指导未来三十年的司法审判实践活动。笔者结合两高解释和两高文章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有关内容,就本罪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之争论进行简要分析,探求两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逻辑和观点,并预测对未来本罪司法实践中的指控和辩护所产生的影响。
02、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之争为何如此重要?
本罪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的争论由来已久。之所以产生如此长期而又巨大的争议,原因在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有两个重要影响。其一是本罪犯罪圈如何划定,是大还是小,是多还是少。犯罪圈划大了,就会框住一些企业甚至是某一同类业务形态的全部企业,可能会对某个行业产生毁灭打击,对整体经济活力产生严峻的负面影响。犯罪圈划小了,就可能要承担“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失职责任。
其二是公安机关的侦查取证责任以及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如何划定。构成要件中的要素少了,侦查和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就轻。构成要件定的复杂了,侦查和指控犯罪的举证工作就难。在“行为犯”逻辑体系下,侦查取证和指控犯罪的工作最为简便,几份“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口供再加上税务机关提供的抵扣税款的客观证据足以指控行为人构成本罪,不需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业务样态,更不需要考虑基于不同税种的征税原理去判断国家税款到底是因逃税而流失还是因骗税而损失。
可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修改《刑法》第205条罪状的情况下,让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权限能力划定本罪的犯罪圈、设定修改侦查指控的举证责任,实现市场主体和司法机关均能接受又符合《刑法》规范的平衡,属实困难。
03、两高认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什么犯?
从两高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表述以及《刑法》第205条的罪状表述来看,两高解释严格遵守了不突破《刑法》的基本原则,仍然沿用了一种行为犯的罪状描述方法,没有添加诸如“以骗抵税款为目的”、“造成税款被骗抵损失”的要素。
本罪行为犯的入罪逻辑看似已成定局,然而最高法却又在反复否定本罪行为犯的属性。最高法文章称“实践中不同的虚开无论是主观方面,还是客观危害性,都差异很大。在起草解释过程中,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结合对罪名沿革历史的考察,对该罪罪状进行了必要的限缩,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合理划定犯罪圈。”“行为犯说入罪门槛低,与该罪的法定刑配置不协调,备受争议,对本罪进行限缩解释成为共识。”
既然最高法认为本罪不是行为犯,是不是意味着最高法认为本罪是结果犯或目的犯?答案又是否定的。最高法文章称“不能由‘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损失’的规定而推论得出构成本罪必须以‘抵扣造成税款损失’为要件的结论”,这就否定了本罪的结果犯属性。最高法文章称“只要发生抵扣造成税款损失的结果,就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骗抵税款的目的”,这就表明最高法认为目的要素并非本罪构成要件中一项独立存在的要素,因此也就否定了本罪的目的犯属性。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最高法认为本罪既不是行为犯,又不是目的犯和结果犯,那本罪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最高法对这个问题有没有明确的答案?我们先看一下最高法文章对这一问题的表达: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核心功能是抵扣税款,只有利用该核心功能进行虚开抵扣,即骗抵税款的,才能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国家财产行为,对其处以重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反之,即便虚假开票,但没有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核心功能的,则不应以本罪论处。”
笔者认为,从最高法文章的上述表述来看,最高法实际上是对本罪行为犯的属性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对入罪的虚开犯罪行为进一步附加了抵扣行为和非法占有国家财产之目的的双重内涵,即虚开犯罪=虚开行为+骗抵税款,骗抵税款=抵扣税款行为+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目的。即虚开犯罪=虚开行为+抵扣行为+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目的。这一观点恰恰与陈兴良教授“非法定目的犯”的观点类似。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刑法》第205条没有规定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因此需要采用目的性限缩方法,将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限于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排除不以骗取国家税款为目的的虚开行为。”“目的性限缩虽然超越了法条语义的范围,但它体现了立法本意。”
至于最高检,则没有过多分析本罪的犯罪属性问题,但是明确认为本罪不是目的犯、结果犯。最高检文章称“《刑法》第205条并未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作出‘目的性’要求”,“不可理解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需具备骗抵增值税税款的目的和造成增值税税款损失的入罪要件。”
04、侦查和指控虚开犯罪的证明责任是否有重大变化?
按照两高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及最高法文章对本罪行为犯的修正观点,在本罪的司法实践活动中,侦查机关调查取证以及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明责任变化不大,但是有了一定的规范框架,附加了一项推定义务。
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指控行为人构成虚开犯罪的,要举证证明行为人有虚开行为、有抵扣税款事实且行为人的不法行为内涵了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目的。由于“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目的”并非一项单独的构成要素,因此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无需就行为人的目的做单独举证,仅需通过行为人的不法行为推定即可。但即便是推定,公诉机关也要完成这项指控工作。如果基于案件已有证据和事实无法推定出行为人有非法占有国家财产之目的,则其指控犯罪的举证责任履行就存在重大缺陷,罪与非罪的审判结果应当倒向有利于被告人一方。
笔者担心的是,由于最高法的态度不够明确,既对行为犯持否定态度,又对目的犯和结果犯持否定态度,但却没有明确肯定非法定目的犯或抽象危险犯。这将导致未来本罪的司法实践大概率会出现这种状态:
(1)一大批司法机关和裁判案例仍然会以行为犯为基准定罪。
(2)少部分司法机关和裁判案例会以抽象危险犯为基准定罪。(关于抽象危险犯一说,可参阅张明楷教授的观点)
(3)几乎没有司法机关和裁判案例再以目的犯和结果犯为基准定罪。
上述可能出现的司法实践状况,所导致的结果是实际上让本罪的入罪门槛大为降低,与两高设想的限缩本罪犯罪圈背道而驰。在两高解释出台前,由于本罪存在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之争,在具体案件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些法院可能就会要求公诉机关举证证明本罪存在税款损失的危害后果,如果公诉机关只能证明有抵扣税款的事实而无法直接证明抵扣的税款就是损失的,就会按照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不按虚开定罪,而是按照非法购买发票等其他罪名定罪,从而达到罪责刑相适应的目的。两高解释出台以及两高文章发布后,由于两高对目的犯和结果犯均持否定态度,且最高法对行为犯的态度过于暧昧,间接认可了行为犯,那么公诉机关就会理直气壮地认为其没有证明有税款损失的举证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犯罪的举证门槛也降低了,被告人出罪的门槛就相应提高了。
此外,这还导致出现一个衍生争议,即谁来承担税款被骗损失的证明责任,谁来给出判断税款损失的标准。公诉机关以本罪系行为犯为由就可以轻松卸掉这一举证责任,法院是审判机关当然也没有举证责任,被告人也不可能去举证证明有税款损失,只可能是积极地举证证明没有税款损失。这样一来,没有任何一个刑事诉讼参与主体要承担税款被骗损失的证明责任。这就导致税款损失这一事实问题必然将失去统一、有效的判断标准,引发实践中更大的混乱。
现在这种混乱的局面就已经出现了。有的案件以抵扣税款金额作为税款损失金额,有的案件以支付的开票费和抵扣税款金额的差额作为税款损失金额,有的案件以开票方取得的财政返还奖励金额作为税款损失金额,有的案件以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的审计或鉴证报告结论作为税款损失金额,有的案件以税务机关出具的说明材料或作出的税务文书结论作为税款损失金额。笔者认为,出现这一混乱和争议的根本原因还是司法机关不敢担责,遗漏规范税款损失的判断标准。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面向。站在被告一方的辩护角度看,对于辩护律师而言,判断税款损失标准缺失的这一重大缺漏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作为辩护一方,在诉讼各方均不愿承担证明责任、无法给出判断标准的状态下,就要主动根据增值税的征税原理总结和分析出正当、合理的税款损失判断标准,向法官讲税法、释原理、明规律、析证据,努力论证税款因逃避而流失和因骗抵而损失的差异,抵扣权益、抵扣税款和税款损失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得出税款损失存在与否的重要事实结论。
 我要补充
我要补充
 0
0

 扫码进入小程序版
扫码进入小程序版
陕西焦点聚光咨询有限公司 陕ICP备18018918号-2